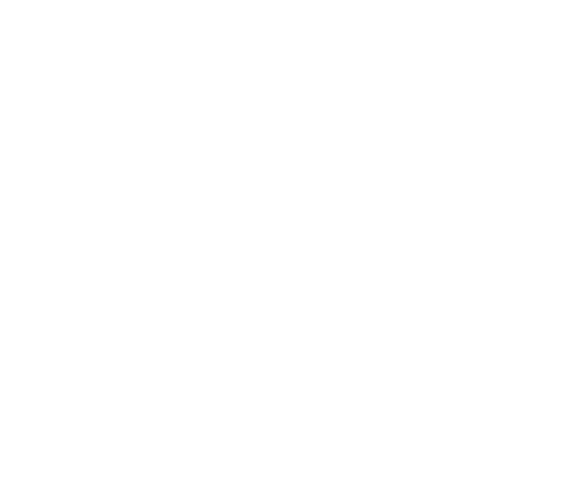山西订婚强奸案入选最高法案例 性同意权的司法突破
一枚订婚戒指,能否成为性同意的“免责金牌”?一场传统婚约,是否天然包含对身体的让渡权?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审判,不仅改写了两个年轻人的命运轨迹,更让“人的权利”愈发清晰可见。从1997年“婚内无奸”的固守,到2019年分居丈夫被判强奸的突破,我国法院正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判决,艰难重构着性自主权的边界。
2023年1月30日,男方席某某与女方吴某某通过婚介机构相识并订婚,男方支付了10万元彩礼和两枚戒指。同年5月1日,双方订婚,次日在新房内发生性关系,女方反抗并报警称被强奸。
2023年12月25日,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席某某违背女方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男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5年4月16日,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法院认为,即使双方订婚,也不等同于法定结婚,不享有夫妻权利和义务。
女方指控席某某在非自愿情况下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并有身体淤青、烧毁财物等证据支持。男方及其母亲质疑女方存在敲诈、骗婚行为,并称未在婚房上加女方名字。法院明确指出,订婚行为虽属民间习俗,但不等同于法定婚姻关系,席某某的行为仍构成强奸罪。
男方已被羁押约690天。女方已退还彩礼及戒指,但男方母亲两次拒领。该案引发公众对订婚习俗、彩礼给付以及性同意概念等广泛讨论。
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的核心是“违背妇女意志”。司法实践中采用“综合标准说”,结合事前态度、事中反抗及事后反应综合判断。本案中,被害人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案发时存在肢体反抗(如拉窗帘、点燃物品)、事后激烈反应(报警、逃离),均为法院所采信。
熟人强奸案常因“自愿性行为”的辩解陷入争议。本案中,法院通过多项证据链(通话录音、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监控视频等)锁定席某某的强迫行为,驳斥“双方自愿”的质疑。审判长特别指出,订婚关系不改变性同意的法律性质,性自主权独立于婚约状态。
尽管婚内强奸在我国司法中仍受限制(通常仅在分居或离婚诉讼期间认定),但本案判决传递明确信号:性同意权贯穿所有亲密关系。最高法相关案例显示,婚内强制性行为的入罪标准逐渐松动,折射性自主权保护的进步。
1997年辽宁省义县法院审理的白俊峰案是中国司法对婚内强奸的首次正式回应。该案中,白俊峰在妻子提出离婚并分居期间,两次强行发生性关系,导致妻子抽搐昏迷。法院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由,认定其行为不构成强奸罪。这一立场与中国古代“夫为妻纲”的伦理传统一脉相承,将性行为视为婚姻的附属义务,而非独立的人身权利。
1999年上海市青浦县法院审理的王卫明案标志着司法认知的重大转折。该案中,王卫明在离婚诉讼期间强行发生性关系,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强奸罪。2019年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法院审理的邓某某案进一步细化了婚内强奸的认定标准。该案中,邓某某在分居期间通过偷配钥匙、捆绑、堵嘴等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法院明确指出,分居期间夫妻已无同居义务,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中国《刑法》第236条未明确排除婚内强奸,但司法实践长期受“婚内无奸”观念影响。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刑事审判参考》收编案例确立了“婚姻状态例外”原则,但缺乏统一司法解释,导致各地裁判标准不一。婚内强奸的核心争议在于“同意”的认定。中国司法实践逐步确立了“动态同意”原则,即婚姻关系不能推定概括同意,需结合具体情境判断。
加拿大R v. Ewanchuk案确立了“积极同意原则”(Affirmative Consent)。在该案中,被告多次进行愈加亲密的身体接触,尽管被害人每次都明确表示“不”,但被告仍在短暂停止后继续推进更激进的行为。法官明确否定“默示同意”,认可她的任何顺从都是出于恐惧。加拿大法院强调同意必须是明确、自愿的表达,即使被害人因恐惧而表面顺从,也不构成有效同意。
根据《民法典》第1042条,法律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司法实践中通常以“附条件赠与”处理。若婚约未履行,法院支持返还彩礼,但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未登记结婚、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
本案中,女方在立案前已将10万元彩礼及戒指退还婚介机构,男方家属两次拒领,法院据此认定女方已履行返还义务,驳回男方诉求。部分舆论将彩礼视为“性交易费用”,认为支付彩礼即默示性权利。然而,法院明确否定此逻辑,强调彩礼仅为婚约象征,与性自主权无法律关联。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彩礼的核心特征为“以婚姻为目的”和“依据习俗”的双重属性。彩礼的认定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以婚姻为目的和依据当地习俗。法院在判断是否属于彩礼时,会综合考虑财物的用途、给付时间、方式、价值及双方身份等因素。
对于彩礼的返还,司法解释规定了以下情形: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的情况,法院会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嫁妆情况、共同生活时间及双方过错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返还及返还比例;已办理结婚登记但未共同生活的情况,原则上应返还彩礼,但具体比例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已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的情况,若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或未共同生活,法院会酌情返还部分彩礼。
有些情绪激动的专业人士认为,对于性自主权的保护会增加诬告风险,且法院对于熟人强奸的认定偏向采信被害人自述。然而,数据显示,中国强奸案的立案率仅为25%,远低于亚太地区50%的平均水平。在被控告的性侵施暴者中,仅有24.9%的人被捕,15.6%的人被判刑,这两项数据同样低于亚太地区32.5%和22.9%的平均值。
美国数据显示,强奸案的虚假报案率不到5%,其他案件的虚假报案率约为2%。这组数据表明,强奸罪的诬告比率并未显著高于其他犯罪类型。这些数据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完善证据收集机制、定罪标准,打破“自认”困境。
事实上,很多强奸案件在立案环节就容易因证据缺失而无法立案;或者即使能够立案,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中,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捕的情况也很常见。性侵案件具有天然的隐秘性特征,多发于私密空间,缺乏公共监控设备覆盖,鲜有目击证人存在,导致直接视听证据极度匮乏。关键证据往往局限于当事人陈述及微量物证,这类证据的时效性极强,特别是生物学证据的DNA降解周期通常不超过72小时,及时提取与鉴定对证据效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我国法院对于强奸案的审理,目前仍沿用“违背妇女意志+暴力/胁迫”的强制模式,要求被害人通过抵抗痕迹、即时报警记录等行为来还原事件情形,否则易以“证据不足”驳回。实际上,尚未到法院审理程序,在受害人报案时,公安部门就会以“反抗程度”来判断是否立案。这一点尚且和国际上已经普遍形成的认知有较大差距。
目前司法实践大多还是采用“婚姻状态二分法”:正常存续期间推定性同意(白俊峰案),非正常状态(如离婚诉讼)可能构成强奸(王卫明案)。中国司法对婚内强奸的认定始终与婚姻状态绑定,这与传统文化中“家和万事兴”的观念密切相关。
强奸罪保护的法益是妇女性自主权,并非贞洁观,这是一种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使妇女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不知反抗的状态,违背妇女意志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
国际人权法将性自主权定义为“不受暴力、胁迫的自由决定权”。本案中,部分舆论对“处女膜未破裂”的过度关注,暴露出“贞洁观”对性自主权的扭曲。简单来说,强奸罪的构成要素在于违反意愿,而非是否造成身体伤害。这也符合国际“性自主权独立于生理损伤”的理念。
如何证明违背意志?在具体标准上,国际上普遍采用“明确同意”(yes means yes)原则,即只有当双方明确表达同意时,性行为才被视为合法。北欧“肯定性同意”规则要求行为人必须确认对方积极同意,沉默即视为拒绝。美国“合理反抗”原则要求被害人证明“足以使行为人意识到拒绝意图的实质性反抗”。中国“不等于不”标准要求被害人通过语言/行为明确表达拒绝,本案中拉窗帘、肢体反抗等证据符合该标准。
比较法视野下,加拿大R v. Ewanchuk案确立的“积极同意原则”已写入21省司法指引,而我国同类案件司法回应率(从犯罪到定罪)仍远低于1/3。该案确立“持续性同意”原则,强调同意需贯穿性行为全程。话剧《初步举证》揭示的司法困境仍在上演:“反抗不够激烈=你情我愿”的逻辑让全球超三分之二性侵案根本走不进法庭。该剧的成功推动了英国法律改革,促使性侵案件审理中“陪审团需优先考虑受害者证词”的条款修订,并被纳入北爱尔兰法官培训及英国警察教育体系。
当传统“家和万事兴”遭遇现代“身体主权”,当“贞洁观”残余碰撞“性自主权”,必然会引起风波,但这最终不会阻碍司法对正义的追求。因为法治正是通过每一次具体的事实认定与规则适用,让“人的权利”愈发清晰、不可侵犯。